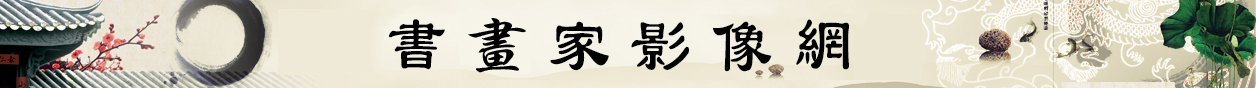
| 时间: 2021-08-31 | 标签: |
论事为人、生活修行,行者与艺术家自来不同。厌弃差别起落,行者乃举平等一如;挥酒情性,艺术家却喜于一事一物中具现风光。因此,以艺入道,艺术家既须断其差别,生命风光乃常不见;由道起艺,行者又往往泥于形式上的文以载道。必得超越两者局限,打破双方疆界,乃有道艺一体的作品可言。
谈道艺一体,即不得不谈禅艺术。禅家的宗风在破、在当下,它既合于艺术家性格的不,更体现着目常功用中的“以偏见圆”。以此,佛教诸宗乃只有禅形成以其为核心的禅艺术,禅诗、禅画、禅庭园、茶道、花道,皆以其样貌清晰,不涉理路,令人神往。
然而,虽样貌清晰,禅艺术所写却不尽然要是禅家禅事。禅原不必于禅者、不必于寺院、不必于僧家的行住坐卧,所谓“尽大地是个解脱法门”,事事皆可入禅,端看你如何拿捏,如何切入。但也因此,寻常人看禅艺术,在虫鱼鸟兽、山水人物中,乃不免雾里看花,艺术家看禅艺术,更常限于理路言,禅诗杰作向为诗家所未识,禅画更往往为画家所误读。
禅画当然不能离画而谈,毕竟这是它在此的外现,但离开了禅来谈禅画,危险恐怕比离开了画来谈禅画要严重许多,《六柿图》就是个典型的例子。
谈禅画,最具代表性的,许多人恐怕都会直指牧溪的《六柿图》,的确,从《六柿图》可以解读禅画的许多特质,但吊诡的是,解读的本身往往就远离了禅,画家,学者在此的误区可真不少。
误区之一是用解析的手法看《六柿图》的构图,以为这构图是几何分析的,却不知结构一一尤其是有意的结构,正背离了禅,如此做,套句禅语,是“死于句下”。
有汉学家甚至将《六柿图》行伸为曼陀罗的表现,以为这里藏着“佛教世界中宇宙秩序的几何图形”,更以为中间体积最大的是“主尊”,到此,就更不知伊于胡底了。
在佛法,密为胜义有,禅为究竟空,一为绝对肯定,一为彻底否定,尽管最后总标举“真空妙有”,但形貌、亲风恰是两极。因此,禅绝不许有如此规范的曼陀罗观。这种汉学家的见解,只能说他还在佛法之外,可这种说法却常被引用,今人不免想到以清微淡远为宗,与密教维叠法相恰好相反的古琴,只因弹琴前有净手、香的规矩,琴桌又被称为琴坛的这些外相,就可被汉学家高罗佩连接到密教对琴有所影响的论述。
误区之二是在笔墨手法上的分析,以此告诉我们牧溪是如何巧妙地安排浓淡不一的六颗相子,于是牧溪不仅是位能掌笔墨的画家,还是一个精心的设计者。这种说法的荒谬,正如将一则公案视为禅师特意安排的教案般,完全不知所谓“箭锋相挂、间不容发”在电光石火之机中映现直观世界的禅家风光。
禅是摒弃作意的,《六柿图》可以从各种角度找出各种关系,但都非禅者的设计,而它的魅力,超越也正在这“无作意”上,没有一个禅者会像学者、画家的分析解释般,那样无聊乃至颜倒。以此下面的“想象”反可能更符合事情的原貌:
金秋季节,柿子红熟,禅院的老和尚怀念柿子的甜味,了小沙弥去买,就在这等待的时刻,恰看到桌上平日的纸墨,于是,聊以排遣,信笔一挥,就完成了这幅千古的绝作。基至我们还可以想象,柿子买来,老和尚津律有味地吃着,却早已忘记了这幅画,直到隔天,再至桌前,才惊觉自己已完成了一幅契于三昧的作品。
这个“想象”与前面的分析相比,似乎少了些“证据”,却更接近禅家的生活。毕竟,离开了无作意这个基点,就离开了禅,以此谈禅画,就有本质的荒谬。
《六柿图》是无心创作的典型,除了随机艺木外,艺术——尤其是西方艺术总有其创作的动机、主题、轴线、结构,但禅认为这都是思虑心、计较心的产物,有其明显的局限,只有契于无心,让内在的佛性流露,才能超越惯性,而到此,就没有哪件事物不是创造的了。
禅谈无心,无心是无有计较心、无有思虑心。人因计较思虑总活在二元分割的世界,追逐攀缘、颜倒梦想,痛苦烦恼、生死轮转皆由此面来,只有将此破除,生命才得以透脱自由,人的潜能也才得以释放,所谓“无一物中无尽藏,有花有月有楼台”,禅生活、禅语言,禅行为之所以如此自在活激、充满创意、当下圆满,正缘于此。
“无心的创作”在东方有特殊的拈提,禅则为其中的极致。而既谈无心,就不能有意解之,分析法在此最为无效。想契入,只能借由同境地的作品相应启发,而与《六柿图》最能相映的,则是禅诗的极致,王维的《辛夷坞》:
木末美蓉花,山中发红萼;
涧户寂无人,纷纷开且落。
这诗白描至极,外缘落尽,无我无人,用禅语来说:即是让“物自性”直接显露,于是,眼前的世界乃第一次以如此直接无隔的面貌映入我们眼帘,我们也如此看到了每一当下的绝对。对这“物自性”赵州从谂的公案说得好:
问: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?”
师曰:“庭前柏树子。”
日:“和尚莫将境示人?”
师曰:“我不将境示人。”
问: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?”
师曰:“庭前柏树子。”
祖师西来意指的是禅的真意,人如此问,赵州却指着自己门庭的柏树回以“庭前柏树子”,问者认为我要的是道,你回答的却是境,赵州则说我从不谈境,再一问,竟又是“庭前柏树子”。
原因何在?因为常人尽管不是视若无睹、听若无闻,却从来只以自己的好恶取舍对待外境,很少“直接地”领略万物,前后攀缘,当下尽失,自然就颜倒梦想了。
所以说,会得《辛夷坞》,就识《六柿图》,契入柏树子,无处非六柿。无论是六柿、是辛夷、是柏树,谈的指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。
上一篇:齐白石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异类
下一篇:神仙中人
最新关注[更多]